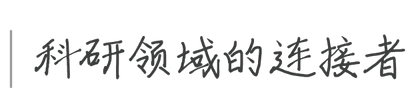南大教授:写了几十年文章,C刊论文只有55篇上下,比较每年发30来篇C刊的大佬,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2025-01-17
2025-01-17
 6756
6756


生命的本意是真诚而又热烈的生活——
“《博士论文札记》座谈会”答谢词 李良玉
承蒙周建超教授和诸位贤达的谬爱,今天专门讨论《博士论文札记》。因为有点急事需要处理,无法分身,作为这套资料的作者之一,我却没有与会。这是一件万分地对不起朋友的事情,内心的歉疚无以言表。借此机会,谨向各位表达诚挚的感谢!
我从1977年初留在南京大学工作以来,迄今48年了。按照当下这个时代的通行标准来衡量,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大学老师,或者说,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教授:上了几十年课,但是,拿不出一份像样的教学奖;写了几十年文章,C刊论文只有55篇上下,比较那些每年发30来篇C刊的“江”中大佬,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不记得参加过多少次社科项目书面评审和会上终评,但是,没有帮自己的学生弄到一个省或国家的项目;当过江浙沪三地多年的社科奖评委,评审组长当过很多次,还多次当过国内其他各种奖项,包括博士论文百优奖的通讯评审专家,但是,却没有能耐为自己的学生争取到一个奖。学生拿到的项目和奖项有许许多多,其中没有我的一点作用。想到这些,我总是感觉深深地对不起学生。
我是一个厚脸皮的老师,无论自己在这个时代多么落伍,从来不曾有过倒霉和气愤的心理。2018年,我在微信朋友圈写了如下一段话:
“社会缤纷,闲者已无兴趣。风雨阴睛,耕者择时而行。江湖滔滔,泳者已成看客。富甲天下,不如手持一卷。”
这是我总结几十年革命经历所得出的经验。它证明,豁达的人生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我坚信,我的所有学生和我有同样的理念。他们从来尊我为“老师”,这就够了。
我今年75岁了,十分庆幸和珍惜与时代有过对话的机会。
在我入职南京大学的第二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之后有过大约30年改革和发展的时光,而最近10多年则被人们称为“新时代”。我和时代保持同步。在改革的氛围里,我始终一贯地申明民主、自由、科学、道德、法治、人权,是中国社会进步和文化转型的唯一正确道路;在新时代,我不遗余力地坚持改革的立场,痛斥时不时泛起的“文革”残渣和社会丑恶现象。这些在我的文章、发言、通信、微信中比比皆是。
面对社会变迁,物换星移,我问心无愧。同样地,应该也够了。我的教书生活告诉我,来自年轻人的肯定和赞扬是快乐的源泉。
1984年,我刚走上讲台不久,给一个本科班上课。同学向教务处反映说,这个老师的讲课,是助教的职称,教授的水平。后来他们班有同学留校当老师了,他是一个见证者。
1993年,我给一个大专班的同学上课。有同学给我写信说:“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无论时空的距离多么遥远,我都不会忘记您!”这位同学毕业之后仍然和我有过书信来往。我不知道NN年之后有没有读者能够读到这些信,如果读到,相信会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我的文集里,公布过一封不完整的回信。其中说:
“你的来信谈到真善美,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作为一名老师,他的责任永远是宣扬真善美,引导同学做正直、善良、卓越的人。但是老师却远不是真善美的化身,也不一定都是正直、善良、卓越的人。就我而言,课堂上自然会给同学留下一点好印象(也许也有坏印象),但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恐怕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所以,同学把对老师的好印象,仅仅建筑在课堂上,有一定的不科学性。”
我相信,这段话对老师的定义是对的。也许,用“好人”“坏人”的概念评价一个老师,难免缺乏辩证法,最好的方法是让时间去慢慢证明吧。
1999年,有学生课后来信说:
“听您的课总感觉淋漓大方,解气消恨。南大没有像您这样的教授,就会变成‘党校’。也许您的风格会对我有深远的影响。”
他是政治系的学生,是一位硕士研究生。
2000年,有进修教师来信说:
“我十分敬仰您的学识,您的授课激发了我的学术热情。我心中识别到了学术一定要创新。您的确拓宽了我的思路,构筑起一种全新的治学风格。”
他来自南方,是某省一位大学老师。
2003年,有学生听完我的课来信说:
“上学期听了您的课,收获很大。您的道德风范和渊博知识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学者大师,也使我在学习和思考中开阔了视野,增加了学识。”
他来自中文系,是一位博士研究生。
2004年,我发表了一篇赞扬匡亚明校长的散文,有读者来信写了一首诗“太多”:
作者简介:李良玉,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当代史和中国当代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