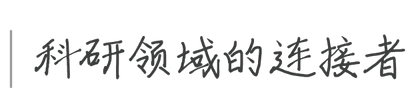公共卫生学:有多少“短板”等待“补齐”
 2020-02-26
2020-02-26
 4767
4767
更多学术热点资讯,关注微信公众号:艾思学术+

“这次疫情实则就是公共卫生人应该冲到前线的,然而公共卫生领域发声真的很少。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都是五年医学专业,但公共卫生职业医生和临床职业医生就是天壤之别,公卫没有处方权。回到这次疫情, 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能做的就是配合命令做好疾病防控,在实验室里做文章……”
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世界卫生组织慢性疾病预防和控制顾问张作风眼中,公共卫生人本应是能够“抓住疯牛鼻子的人”。然而,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公卫人的表现,近日一位公共卫生体系从业者的上述评述,却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学科从人才培养到体系运作所面临的困境。
“在任重道远的抗疫之战里,中国卫生防疫管理架构和公共卫生现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张作风说。
与健康最紧密的学科却最被忽视
传染病,包括霍乱、麻风病、结核病和疟疾等,曾经是影响我国公众健康水平最重要的疾病。通过建立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开展预防接种和爱国卫生运动等防控措施,我国降低了传染病发病率,重点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而当这些流行病或地方病淡出人们的视线时,临床医学就日益凸显出其重要的地位。
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疫情的到来,让人们重新意识到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性。2002年建立起来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CDC),到2007年已拥有国内各级疾控中心3500多个,全职人员共近20万人。
同时,“公共卫生的范畴也越来越广。从前主要集中在传染病的防控上,现在延伸到了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非典之后,高校公共卫生学科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浙江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学院院长吴息凤在接受采访时说。
然而,随着非典疫情被淡忘,各地政府与医院重新将数字量化的临床医学提到更为重要的位置,处于上游的公共卫生学科与体系建设却几乎无人提及。
2018年,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姜庆五主编的《中国公共卫生概述》正式出版。书中提到,“总体来看,中国专业公共卫生人才数量配置不足、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实际上,每年真正需要临床医学医治的人群,只占一个国家人口数量的极少数,绝大部分人的健康问题都需要公共卫生体系的保障。“除了突如其来的流行性疾病、慢性病,人们的营养健康、生活环境对健康的影响、职业病等都属于公共卫生范畴。”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杨蓉西告诉,“相较而言,临床医疗面对的是个体,公共卫生面对的则是群体。”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每万人口中,仅有1.4名疾病预防控制人员,相当于美国的1/5;食品安全、健康教育、妇幼卫生、采供血人才缺乏;卫生应急人员主要分布在卫生行政部门、监督部门、高校和研究机构,目前十分缺乏应急管理人才和专家,大量卫生应急人力需要培训。
需求激增与人才流失
与大量公卫人才的需求缺口相比,公卫人才培养则显得有些势单力薄。
目前,我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下,包含预防医学、食品卫生与营养学等多个二级学科,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等80余所高校也都设立了公共卫生学院,但这一数字与我国2900多所大专院校的总体数量相比,相形见绌。
2019年6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召开的“中国医改十年: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更是直指目前疾控系统的人心浮动和人才加速外流的现状:“近三年来,仅国家疾控中心流失的中青年骨干就有百人之多,有些地方疾控机构的人才流失可能更严重。”
一些高校公共卫生学科的学生,在就读期间就想转专业,很多人希望转到临床或其他学科。专业学习人群的不稳定,导致最后真正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人并不多。“出现这种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待遇较低、地位不高。如果从事公卫工作,待遇比不上临床或者其他专业,有些学生可能就不会把公卫专业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吴息凤无奈地说。
这种情况在北京大学也出现过。据该校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刘继同介绍,本科期间,公共卫生专业就不是主流。尽管在招生时都属于医学类招生,但在本科学习两年后进行专业分流时,大部分学生都会选择临床专业,很少有人主动选择公共卫生专业。
收入水平较低是其中一个原因。2005年,一项关于公共卫生行业薪酬的调查问卷显示,中国多数基层公共卫生工作者,特别是年轻的公卫从业者的待遇,仍徘徊在最低工资标准的门槛上,甚至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同等资历中国公卫从业者的收入与美国相差近40倍。在1420份调查问卷中,高达47%的受访者后悔进入公共卫生行业学习或工作。
与人才流失并行的是系统内人才评价标准的错乱。科研导向与实用导向混淆不清也是造成公卫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刘继同认为,这导致现在很多公共卫生学院的教师将大部分精力花在实验室和基础医学研究上,渴望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却很少有学者真正关注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建立和政策、体制机制等重大现实问题”。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陆家海接受采访时也提到,我国疾控中心的职能过于集中,导致人员身份不够明确,在“公务员、执法人员、科研人员”间纠缠不清。
在德国有着多年学习与临床经验的杨蓉西认为,目前我国公共卫生机构普遍侧重研究而非服务;同时,基层人员与普通百姓也普遍缺乏公共卫生常识。
“其实,公共卫生是交叉学科,是预防与临床医学高度一体化的服务,如今却被人为割裂为医疗与公共卫生两个体系。这也让公共卫生学科在以临床学为主的医疗系统中,失去了话语权。”刘继同说。
不仅是疾控中心,“在高校中,公共卫生学科目前的定位也多偏向实验室研究领域,忽视了它的基础性与政策性。”刘继同坦言。公共卫生学科的基础性人才主要使命是,为建立并完善社会公共卫生体系提出建议。“公共卫生体系就像是军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杨蓉西则将公共卫生系统比作国家的润滑剂,“它不是一个单独的领域,而是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环环相扣。公共卫生是宏观的,也是所有环节的黏合剂”。
亟待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
“我国社会发展要实现现代化,医疗卫生体系也不能例外。而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健全程度,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健康服务体系的现代化程度。”刘继同说。
1997年夏天,美国曾经历过一次史上空前的“反烟运动”,这项运动取得了“美国公共健康方面最具历史意义的成就”。美国的烟草业代表同意偿付3685亿美元,用作吸烟直接或间接导致的疾病治疗费用。这笔赔偿金还作为反烟团体的青少年禁烟宣传、健康研究、教育计划资金来源。此外,美国的公路安全运动减少了公路死亡人数;定期健康改善运动则着重于健康的饮食和体育活动,同时还推动了社区花园和基于人口的肥胖预防行动。
而在我国,18岁以上居民近84%从不参加业余锻炼,近81%的家庭人口每日食盐摄入量等超过健康标准……
陆家海认为,公共卫生专业性很强,所以要稳定一支强有力的公卫人才队伍。“这支队伍必须要以具有临床医学知识的专业人才为基础,同时吸纳更多不同领域的人才”。
“与国外大部分公共卫生学院培养研究生相比,我国从本科就开始培养公共卫生人才,且临床医学基础更有优势。”吴息凤认为,“未来,高校需要进一步重视公共卫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无论是专业型还是学术型。同时,希望公共卫生人才拥有多学科背景,特别是临床医学的背景。如此,疫情发生时才能更好地为疫情防控服务。”
吴息凤提议,在进行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时,还可以考虑另外建立一个“4+3”的培养机制。即前4年学习医学和公共卫生学,后面3年进行全科医学规培,由公共卫生学院来培养全科医生。因为全科医学主要面向社区人群,需要有预防医学的相关知识,由公共卫生学院对这部分人才进行多学科培养后,可以给予其参加临床执业医师考试的权利。
国际上,关于公共卫生人才体系如何建设的话题尚未有定论。“高校是否需要设立公共卫生学院,或由各方临床人才集合组成公共卫生系统,是很现实的问题。”刘继同说。
杨蓉西也认为,目前我国具有临床经验的公共卫生学科教师不多,如果能让公共卫生学科的学生有更多临床实习的机会,让他们能更好地理解临床医学和临床上遇到的现实问题,就可以更加有效地从临床现状出发建言公共卫生管理,或者应用到公共卫生工作实践中。
但不论哪种方式,学习医学的学生都应该具备公共卫生的知识储备。一些欧洲国家并没有在本科期间设立公共卫生学院,高校公共卫生学科也只培养研究生。这一专业招生时并不局限于医学专业,而是面向各个专业,“欢迎各领域人才进来,才能让更多人了解公共卫生领域,同时让公共卫生领域拥有更多复合型人才”。刘继同认为,高校应该将公共健康课程作为必修课,让所有高校学生都接受公共卫生的基础教育。
多方协同
“在德国,公共卫生在服务层面的体现更像是一个社会学科,其面向的不仅仅是高校,而是从中小学教育抓起,从小培养他们对健康和疾病的认知。”杨蓉西介绍道,“有时候改变成年人的思维很难,成本也很高,那就从娃娃抓起。孩子学会后,可能会影响家长的生活方式,一举多得。这就好像流感高发或雾霾天气时戴口罩,往往是年轻人敦促家中长辈这样做。公共卫生教育和对健康的认知,与植树造林一样,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
除了面向多学科的学生外,公共卫生学还应该加强对基层医务工作人员、社区诊所、小医院、居委会或者街道办事处等社会人员的培训。“当疫情发生时,社区的防控与家庭防控急需这类人。但他们首先需要具备基本的公共卫生知识,才能做到信息顺利上传下达、措施不偏不倚地执行,同时具备自我防护的相关知识后,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人。”杨蓉西说。
国外也是多方力量协同进行公众的健康管理。如家庭医生、区域医院、保险公司、专项的体检机构等,都从生活方式、慢病治疗、健身康养等各方面予以支持。
此外,德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纳入社会管理体系,涉及的不仅是公共健康,还有经济发展状态、公共关系、社会心理等,因而会根据社会发展和公共需求对法案以及管理方案进行修订。修订时,往往会采纳多方的意见,如政府官员、临床医生、公共卫生专家、基层工作人员,还包括私人企业家、律师等不同背景的人士。
“在我国,每个省份都可以考虑建立公共卫生专家库,但需要注意的是,专家库中的专家首先要吸纳具有多专业不同层次的人,并保证发言是平等的。”杨蓉西强调。
多层次人才不应局限于医学界和学术界,还应包括产业界和法律界,“产业界中不应只邀请国企,还应该包括民企,另外还要考虑到乡镇企业。”杨蓉西建议,“多层次人才共同参会,才能将某一事件还原得更接近事实。同时,在制定处理方案时,方能考虑社会各阶层人员的需求,以及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需要,这样才能让公共卫生系统在最终运作时更好地达到为公众服务的目的。”
另外,公平是公共卫生系统另一重保障,不能唯权威论,因为团队中有教授或者院士,就忽略其他人的声音,“更不能因为某些领导的倾向性就众口一词地赞同。团队对于成员的献言献策要有一定的包容性”。杨蓉西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会议在政府较高级别领导的主持下定期召开,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甚至不需要面对面,电话会议也可。
不过,最终能够让更多人参与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根本动力,是让参与者感受到公共卫生学科的价值,“以及较好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杨蓉西说。
走出高校围墙
除了吸纳多元领域的人才,公共卫生学科还应该主动走出高校的围墙。美国高校医学学者可同时供职于疾控中心。当紧急情况发生时,疾控中心首先“拉响警报”,而后的研究工作则由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实验室完成。
“让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参与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和教学中来,同时也让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师生参与到疾控中心的大数据分析中去,这样不仅可以提升数据价值,改善师生实践能力,还能提高疾控中心的科研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多方共赢。”吴息凤说,截至目前,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已与杭州市疾控中心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探索高校附属疾控中心的新模式,希望能够为公共卫生学科建设改革开个好头。
吴息凤认为,当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时,疫情的防控首先要依靠专家、依靠科学。决策过程要依靠公共卫生的专业知识。最重要的是建立更完善的公共卫生体制机制,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保障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在防疫中的作用,推动公共卫生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非典的成功防治就得益于流行病学专家和疾控专家的献计献策。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希望能有更多的公卫专家勇挑重担,积极参与其中。我们需要让公卫专家在疫情防控中发出更多声音。”吴息凤说。
在刘继同看来,只要将公共健康卫生问题真正融入中国发展战略中,上述问题便能得到切实解决。“我国曾提出‘健康中国’的国策,但没有人真正意识到如何有效地保证健康。”刘继同说,这次疫情提醒决策者乃至每个人深入思考什么是“健康”?什么是“健康中国”?我国医药卫生体系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如何保障医学教育、公共卫生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体系更好地发挥作用,妥善处理行政权威与专业权威关系,摒弃行政化带来的影响?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中也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因此我认为,应该进一步提高公共卫生的地位和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吴息凤说。
作者:袁一雪
版权申明:本文来源中国科学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文章转摘只为学术传播,如涉及侵权问题,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