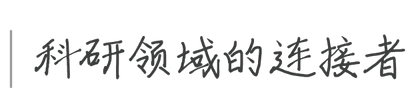写作和科研一样,终是“不孝”
 2019-08-27
2019-08-27
 6888
6888
“中文系?你搞什么?”
“没钱途的。换换吧。别让家里人操心。”
“中文系干嘛的?学文学有什么用?”

在选择了学中文这条路之后家里联系的不联系的亲戚朋友都直白或间接的向我投来了这类的问题。
“哎,好好的青春几年,怎么就白浪费了在这些没用的东西上头。”
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一遍一遍的强调,不是这样的,中文是我的初心和兴致所在,中文有它的用处,这个专业在我接触一开始就方方面面的影响着我面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中文的研究虽然不像理工有实验和数据,可我们一头扎进书籍文字和戏曲剧本也一样要下苦功夫,也会在复杂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经历中挣扎着尝试深层的理解文章的时代价值和挖掘现实意义,要在跨越了几个世纪的文本里探索,要学贯中西,要通晓古今。
可每次我说“没有没有,我就是喜欢中文”的时候内心总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提醒我——“你本可以有一个另外的选择,你本可以去学热门专业的”。

我知道学中文不等于“培养作家”,但我是抱着一颗“成为作家”的心选择的这个专业。
踏进去就越陷越深,写作课不过是一门不太重要的小门类。毕竟它的大名叫做“汉语言文学”,该钻研的还是文学群体、文学思潮、当代各种不断涌现的文学问题。
但是毕竟还是要写的。即使论文报告实在称不上是文艺作品,我也尽力把它雕琢的用词精准优美,语句通顺华丽。不过是些无用功,但总要在枯燥的生活中找到乐趣不是吗。
我想起张怡微在《我自己的陌生人》中写过:“当作家本身就等于选择了一种不孝。”这是一句太能打动我的话,不仅是写作,读研、读博、选择科研深造这条路都等于选择了一种不孝。
因为这份选择不仅仅是选择在青春正当头的时候窝在图书馆或实验室,过着和食堂寝室三点一线的生活,牺牲很多社交和娱乐换取在书本里的那份执着和安心。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中文系的这个选择最后能不能当成作家,但是“不孝”这个罪名已经成立了。
身边的姐妹陆陆续续当老师的当老师,考公务员的考公务员,实习和兼职的钱以及足够在临近新年的日子里给爸妈置办一身新年的衣服,再给家里买买年货了。
而我学费还是爸妈在掏。

玛格丽特·杜拉斯曾说,“我独自一人在房间里,花园里只有猫和鸟,寂静之下,我开始写作。”
青年作家郝景芳也在采访中表示“写作是孤独深处最重要的情感力量。”
埋首科研20载的任咏华直言:“在香港做科研是一条孤独的路。”
写作和科研一样,都是孤独的。可我不怕。
这就是我在写作和科研这条路上仅有的一点点天分。我唯独怕自己做的不够真诚,仅此而已。
而时至今日我才慢慢明白,我这点执着的纯粹其实是很难得的。
因为我的这份不管不顾的真诚,所以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挚友就不得不为我担心许多我没怎么考虑的问题——我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生活的时候,他们替我忧虑我的生存问题。
“所有你现在的轻松,都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我这才深切的体会到。

他们小心翼翼在保护着我,让我写让我学。但是偶尔也会旁敲侧击的问我会这样一直写下去吗,考不考虑读博,要不要试试看找找工作呢,有没有固定的读者了,不要总把自己闷在书桌前和图书馆了,有关LGBT等敏感话题写起来安全吗……
我当然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在社会中摸爬滚打几十年,在他们看来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学生娃。
他们让我安安心心的呆在象牙塔,把生活的奔波和苦涩藏起来,但又时不时的透露一点给我。
其实我怎么会不懂呢,他们太想保护我,又怕我在象牙塔待得太久,适应不了喧嚣社会——毕竟会有很多人会说“没钱途”“没用”,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这样,其实也不理解,但是双手投降的 站在我背后支持我的选择。
哪怕我选了一条“不孝”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