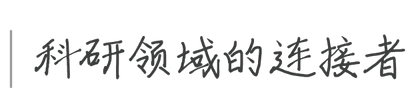复旦教授:在一般院校里,我可能连当副教授都不够格
 2024-06-14
2024-06-14
 5927
5927
信息来源:《中华读书报》专访姚大力教授文章
一个写了八篇文章的人,就一定比只写过六篇的人水平更高吗?
复旦姚大力教授在一次采访中分享了自己对现行学术量化考核的看法,他还表示,我是很幸运的,毕竟如果在某个一般院校里,我可能连当副教授都不够格。
问:您的学术经历很有意思。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您担任过四年系主任,到1991年卸任时却还是个副教授。这么多年以来,您从没有出版一部个人专著;已出版的《北方民族史十论》《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读史的智慧》等书,其实都是您已发表论文或学术评论的结集。在中国的学术界,这好像有点另类吧? 姚大力:很多年以前,复旦一份叫《复旦青年》的校内报纸有记者采访我。那篇访谈稿选用了我当时说的一句话“我是很幸运的”来作标题。这是我的真心话。因为如果在某个一般院校里,我可能连当副教授都不够格;但到复旦不过两年,我就被晋升为正教授。 在最近二十多年里,我很可能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未出专著就获得正教授职位的人。不仅如此,讲老实话,在晋正时,我正拖欠着在南京大学时认领的一个教育部科研项目,并且已拖了好多年。所以我一直被挂名在教育部的“黑名单”上,不允许再申报新的部颁课题。 我做了十几年副教授,并没有热锅上蚂蚁那样的焦虑,没有感觉到因为不是正教授就被别人看不起,而且活得也还算可以。但若不是复旦对我“破格”,我大概只好在副教授的岗位上退休了。 同时也应当感谢南京大学对我的包容。我从1981年开始读博士,直到1986年底通过论文答辩,其间足有五年多。当时没有什么别的人读得这么长的。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都感觉单纯得不可思议。 虽然几乎从一开始就大体确定了博士学位论文主题,但事实上有很多年我都没有把精力真正集中在论文写作上。除了花很多时间修习法文、俄文等外语课程,我几乎一直是在由着性子东找西找地挑书读。 我的硕士导师和第一任博士导师韩儒林教授于1983年去世。此后我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翁独健教授门下。两位好像都对我很信任,任由我尽情读书,从没催过我赶快写完论文毕业。但等翁先生于1986去世后,南大和民族所两方面的老师们就觉得我再拖下去有点不对劲了。我想请蔡美彪教授继续做我的论文指导教师。他大概也觉得不太对劲,建议我不必再另寻导师,只是督促我赶快写论文,并同意将来做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这才逼得我连忙转过身去,在翁先生逝世当年写完论文,并通过了答辩。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过去只是“由着性子”读过的各种书籍,实际上大多数都会在后来所从事的研究中被派上用场。就好像当时无意中撒在水里的许多网,日后无论拉起哪一张,都会有满满的收获。由一个人的直觉导出的诸多学术兴奋点或兴趣点,虽然从表面看来可能相互孤立而缺乏联系,其实在与他的学术个性最匹配的那个特定智识结构中,往往都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研究生时代单纯的读书生活,让我至今留恋当年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那间塞满古书和外文书刊的屋子。 在研究生时期教过我的老师中,还有人能够从古代经典的随便哪一句开始,流利地接着它背诵下去。你提一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他就能不加迟疑地往下背:“禹傅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随着从幼年起就接受“记诵经传、句读文义”的传统教育方式的人们纷纷凋谢,今后的学生再也不可能碰到这样的老师了。 在当时的南大操场上,每天早晨都能看见许多正在锻炼慢跑或散步的老先生。他们中间很少有像今天的名教授那样西装革履、行头笔挺的,大多是一身中山装,甚至还皱巴巴地稍嫌邋遢。可其中属于最响当当的大师级学者的绝不在少数。 比如我常见到一位矮小而貌不惊人的老先生,就是中国最权威的法国文学专家。他一直招不到博士生,因为他出的专业试题,竟要求考生把《诗经》里的选篇译成法文。学法文的年轻人自然读不懂《诗经》,连其中的汉字都认不全。出这样的考试题目,哪还能招得到研究生?在操场跑道上,你可以与大师常川相遇。这是何等令人心仪的日子啊! 真的,只要面对着这些老先生,你就不能不被体现在他们身上的那股充沛的人文精神所感召。但是我们还能把它继承下去吗?我们这一代,其实是“接轨的一代”:一则要跟中断了数十年的本国学术传统、治学方法接上轨;二则要跟同样长期地被疏离的国际学术接上轨。对基本上属于“半路出家”的我们这一代,这种承上启下的使命沉重非凡。 所以需要想一想,当我们自己也在慢慢地变老的时候,我们能留给下一代的是什么?在下一代想起我们的时候,除了互相间那种鸡肠狗肚的争斗,除了看见我们在谈车子、谈房子、谈票子、制造一座庞大无比的精品垃圾山,我们还能留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更值得纪念的东西? 问:这么说来,您还真的十分幸运,竟然没有被日益严峻、甚至似乎有点恶化的学术竞争和学术生态“hold”住。 姚大力: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干扰。有时我会忍不住。我不止一次在学校会议上发牢骚说,自己代表了学术上的弱势群体,但希望学校不要把弱势看作就是弱智。不过叫归叫,更关键的,还得要有一种沉静的心态。既然自己确实低产,你就不能还那么在乎,事事要与人争一日之高下。那就回转身来守以淡定吧。 早在进入专业领域后不久,我为这辈子设定的目标,就是要在蒙元史和北方民族史领域的一些重大题材上,写十几篇大型的、三四万字的第一流论文,让后来的研究做不到轻易绕开它们。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事实上,我至今还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我一向没有撰写专题著作的打算。 最近虽已动手把开设“北方民族史文献讲读”课程的讲稿改写为书稿,但那至多也只是一部综合性的“疏论稿”,算不上“专著”。这意思不是说写专著不好,更不是要反对别人写书。但我觉得健康的、多样化的学术生态,应该平等地允许并鼓励人们去从事各种各样在形式与风格上互有差异的学术活动。不写书的人就一定比写书的人来得弱智吗?我绝对不相信。 但是我担心的是,现在盛行的这套科研项目化、评价数量化、育人明星化、棋艺盘外化的规制,会把太多的年轻学者们“hold”住。不是说这些规制一无是处。可是,学术研究真的都可以像鞋匠那样预先制订生产计划、接受主顾的预约和定金、按部就班地投入制作、如期交货并结清余款吗? 历史学的讨论需要多学科的视角,但学者们也早已意识到,遏制它自身的人文科学的根本属性、将它完全“社会科学化”,只会无止尽地伤害这门学科的价值和魅力。把学术研究活动压缩在“项目”范围内,实际上是把属于课题研究后期的“成果产出”阶段与研究者于此前早已投入其中的在自身技能提高、知识更新、素材积累、思想酝酿等方面必不可少的长时期学术准备阶段强行剥离开来,并且根本不承认后者的存在。 在量化考核压力下接二连三地认领和实施这样的项目研究,极不利于青年学者的健康成长。不少地方把一个人的各种学术成果统统折合成“工分”加以衡量比较。多发表一篇文章就多两分;某甲的书比某乙的书早出版一年,也可以因此多得两分。 但是一个写了八篇文章的人,就一定比只写过六篇的人水平更高吗?一本早出两年的书,其评价就必定应当高于比它晚出的书吗?对一个青年人来说,究竟是应该抓紧一两年时间多写几篇文章,还是首先巩固或提高、甚至再新学一门对他十分有用的外文更重要? 大概因为太多的“人情”关系,人们越是怀疑对于学术成果品质的任何权威评定的公正性,就越是只好求诸数量指标,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各种荒唐的“可显示度”,如大部头、多卷本、系列著作等等。这种局面若不改变,必将贻害无穷。